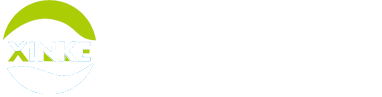日化废水虽属有机废水范畴,但其特殊化学组成显著区别于食品、制药等行业。不同成分不仅决定污染物浓度,更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、工艺选择与系统稳定性。理解这些成分的作用机制,是科学设计处理流程的前提。
一、表面活性剂:泡沫与生物抑制的双重挑战
阴离子表面活性剂(如LAS、AES)是日化废水中普遍的成分,浓度常达数十至数百mg/L。其两亲结构易在气液界面富集,导致生化池或气浮单元产生大量稳定泡沫,影响设备运行与操作环境。更重要的是,高浓度LAS可破坏微生物细胞膜通透性,抑制其代谢活性,尤其对产甲烷菌毒性显著。当LAS超过50 mg/L时,需强化预处理(如气浮)将其降至安全阈值,否则厌氧或好氧系统易出现降解效率下降甚至崩溃。
二、油脂与香精:传质阻碍与毒性风险
动植物油及矿物油在废水中以乳化或溶解态存在,易在生化污泥或膜表面形成疏水层,阻碍氧气与底物传递,导致DO异常升高而COD去除率下降。香精成分复杂,多含萜烯类、醛酮类等难降解有机物,部分具有抗菌性(如柠檬醛、肉桂醛),即使低浓度也可能抑制硝化菌等敏感菌群。这类物质难以通过常规生化矿化,常需前置水解酸化或后接深度氧化,才能保障出水稳定性。
三、高碱性与盐分:微生物环境的隐形杀手
日化生产常用NaOH、碳酸钠等调节pH,导致废水pH常高于9。强碱性环境会破坏微生物酶系统,尤其影响硝化过程(理想pH 7.5–8.0)。此外,部分产品含无机盐(如氯化钠、硫酸钠)作为增稠剂或防腐助剂,高盐分(>2000 mg/L)可引发渗透压胁迫,使细胞脱水失活。此类废水需在调节池中中和并稀释,或采用耐盐菌种,否则生化系统启动困难、运行波动大。
四、防腐剂与螯合剂:难降解与金属干扰
MIT、CMIT、苯氧乙醇等防腐剂设计初衷即为抑制微生物,其残留对废水处理菌群构成直接威胁。EDTA、柠檬酸钠等螯合剂虽本身可生物降解,但能与重金属形成稳定络合物,一方面延缓金属沉淀,另一方面可能增强重金属生物可利用性,间接加剧毒性。这类成分要求系统具备足够长的水力停留时间或强化氧化预处理,以破坏其分子结构。
五、色素与增稠剂:色度与粘度的运行负担
染料多为偶氮或蒽醌类化合物,结构稳定、色度高,常规生化难以脱色,易导致出水感官不达标。增稠剂(如卡波姆、黄原胶)大幅提高废水粘度,影响固液分离效率,使二沉池沉降性能变差,SVI升高。高粘废水还易造成膜污染或堵塞布水器,需通过混凝或氧化预处理降低其分子量与粘性。
六、可生化性波动:工艺弹性的核心考验
日化产品配方多样,不同批次废水BOD₅/COD比值可能从0.1骤变至0.5。低B/C废水意味着大量难降解有机物存在,若直接进入好氧系统,不仅处理效率低,还易积累惰性污泥。此时须引入水解酸化或厌氧段,将大分子“打开”,提升可生化性。工艺设计需预留足够弹性,以应对水质的不确定性。
日化废水的处理难点不在“高浓度”,而在“复杂性”与“抑制性”。每一种典型成分都可能成为系统失效的诱因。唯有深入理解其物化特性与生物效应,才能在工艺选择、参数调控与风险防控上做到有的放矢,实现稳定、效率高、可持续的治理目标。